
【摘要】媒介是人与自身外部世界的中介。媒介形态变迁经历了具身化、体外化和技术具身化三个阶段,表征着三种不同类型的传播形态和社会形态。媒介伦理是在不同的媒介形态和传播形态中,人们通过媒介而形成的关系准则。新传播媒介介入人们的日常实践,意味着媒介伦理生发出新的内涵。技术具身时代,人与媒介的关系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伦理关系。
【关键词】中介 媒介形态 传播形态 媒介伦理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人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中,这种种关系,便是种种伦理,即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由于媒介是人与人、人与自身外部世界关系的中介,人的行为都在媒介中展开,因此,所谓媒介伦理,就是在不同的媒介形态和传播形态中,人们通过媒介而形成的关系准则。近些年,5G技术、物联网、VR等和互联网技术一起,正加速介入人们的日常实践,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因信息网络的重新连接而重组,这意味着人们与其赖以生存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变,也意味着媒介伦理生发出新的内涵。
媒介形态变迁:人与世界关系的视角
何谓媒介?根据威廉斯的说法,媒介(medium)首先是指“中介机构”或“中间物”,即一种感官(或一种思想)要去体验(或表现)所必需的中间物;其次是指技术层面的不同媒介(media),例如声音、视觉、印刷等;第三则指资本主义,如报纸或广播事业被视为另外事物(例如广告)的一个媒介。[1]但“第一层含义始终贯穿于后二者之中”,亦即“只有被当作‘体验(表现)’的中介物,才能被当作媒介(居中搭建关系、转化关系之枢纽)”。[2]因此,媒介就是现实世界中诸多现象相关联的方式,也指“实现跨时空社会交往的不同技术与机构”。[3]也是在中介的意义上,麦奎尔如此定义大众媒介:它“参与了最广义的符号意义上的知识的生产、再生产和分配,而这些符号与社会经验具有密切关系”,从而“在客观社会现实和个人经验之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4]作为中介者的大众媒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机构以及人与人之间起着作用,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的中介。因此,传播媒介的核心就是中介性,是人及人的活动得以展开的方式,其意义在于建构、协调人的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以媒介为中介的信息传播、沟通交往活动,也就是库尔德利所说的媒介实践——“人通过媒介做什么或是做什么与媒介相关的事”。[5] 如此,媒介便是人们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
人与自身生存的外部世界的关系,即人能否及如何把握、改造外部世界,是所有哲学家要回答的问题。传统社会,人以自己的身体接触、感知外部世界,与世界的关系是直接的。进入工业社会,机器取代人的身体介入到人与外部世界之间,成为人通向外部世界的中介。以机械化(印刷机)、流水线(新闻生产流程)为基本特征的大众媒介,不仅使人的身体“隐退”,而且也重新构造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当下,数字媒介和生物体的身体“互嵌”参与人的实践活动,又一次改变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媒介形态变迁的过程,也就是人与外部世界中介关系的变化。
将媒介视为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中介,“媒介史同时也就成了人类史”,[6]反之亦然,于是,“媒介理论就是媒介史的产物”。[7]麦克卢汉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主导的媒介”,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口语传播时代、书面传播时代和电力传播时代;洛根在此基础上将传播史划分为非语言的模拟式传播、口语传播、书面传播、大众电力传播和互动式数字媒介传播5个时代。[8]基特勒依据人类传播的“编码”方式,将传播媒介的历史切分为文字媒介和技术媒介两个阶段。[9]延森则从媒介的物质性和特定媒介及其传播实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出发,将媒介划分为三种类型:作为人际交流媒介的人的身体、经典的大众传播媒介以及数字化的信息传播技术。[10]我们从媒介与身体的关系以及人获知身外世界经验的不同实践类型出发,将媒介划分为具身媒介、体外化媒介和技术具身媒介三种形态。
媒介形态、传播形态即社会形态
媒介形态的不断演化,也就是人与外部世界中介方式的变化,意味着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机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换。
首先,具身媒介产生的是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和传统社会形态
在前现代时期,人们依赖生物性身体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交流等日常实践活动,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是直接的。人们依靠身体的在场进行面对面的传播,用耳来听,用眼来看,用四肢、皮肤来感知,用口语、动作、表情来传情达意,人的身体及感官充当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中介,即具身媒介。人通过身体采集、加工、传播信息,使得身体集生产性、传播性与接收性于一体,完全参与到人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之中。
具身媒介实践和面对面传播形态,意味着实体空间是传播不可或缺的要素,或者说面对面传播就在实体空间中展开,从而决定了社会的组织方式和外在形态。拥有身体中介的个人,因血缘和面对面传播与熟人之间形成家庭、家族等社会关系形式,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因此而展开。以身体在场为前提的面对面传播,是“一个相互的、持续不断的、协商的、合作建构意义的交流过程”。[11]在这个建构、共享意义的传播过程中,人不仅造就了自身,也在双方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各自对对方产生了行为期望,人与人的关系得以形成。因此,身体在场的面对面传播自然也是传统社会形态的表征。
其次,体外化媒介形成的是大众传播和现代社会形态
现代社会或称工业社会,“是一个通过技术手段来调节人类与周遭自然世界的关系的社会”,“工业化改变了人和自然的关系”。[12]自机械印刷机出现,传播媒介开始从人的身体分离,人与人之间有了物理性媒介——印刷机、电报、电话、电影、电视等,它们都以体外化媒介的形式将人们隔离开来,介入人们的传播实践,成为人通向外部世界的中介。体外化媒介将身体从传播中抽离,传播形态随即改变——大众传播是一种无身体的传播。
技术媒介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技术媒介一方面扩大了人的经验范围,拓展了人的生存时空,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宽广的时空却使得人自身难以抵达,反过来又要借助技术媒介这一中介。如此,在人和无法为其所直接感知或接触的自然之间,和其他社会机构之间,以及人和人之间,新的关系便因作为中介的技术媒介而形成。
第三,技术具身媒介使得身体“回归”,人及中介本身发生了变化
以数字化、交互式为特征的融合媒体应用平台出现,又一次改变了媒介形态。这些融合媒体平台具有整合原有媒介形态的属性,将原有的媒介链接到了一起,自然也就整合了所有的传播形态——“由网络化的个人计算机和手机之类的数字媒介构成了第三维度的媒介,它们整合了‘大众传媒’和各种不同类型的人际传播”。[13]不仅如此,5G技术和物联网的应用意味着一个万物互联的“全连接”社会到来。这种连接关系,不是具身媒介时代人与人、人与世界的直接感知,也不是体外化媒介时代以信息流动而连接的信息关系,而是数字媒体时代的终端与终端的关系。就社会意义上来说,就是新型的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
而人工智能、VR/AR、生物量子芯片等技术,正引发新一轮媒介融合,“不仅止于媒介形态之融合,也不仅仅是社会形态的融合,而是技术与人的融合”,“技术确实要潜入人的身体,成为主体的一部分”。[14]新传播媒介并非体外化媒介,而是人的“器官”,它积极介入人们的身体经验,成为和人的身体融为一体的技术具身媒介。技术具身媒介既不单单是人与外部世界的中介,亦非生物体的人,或区别于传播客体的主体,而是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整体关系,甚至是一个复杂的环境——一个融合了媒介、内容、收受主体、传播等要素的环境,而人就在这个环境中呈现自身这个复制品。
公民素养:技术具身时代的媒介伦理
在具身传播时代,虽然身体“到场的追求未必使你进入对方的心灵本身,然而它的确可以使你接触对方的身体”,“朋友和亲人的身体至关重要,面孔、嗓音和肌肤具有接触的感染力”,[15]人们以面对面传播来寻求意义的共享和关系的建立,共同面对未知世界。因此,真诚、互信、互助、推己及人是最基本的伦理要求。在以体外化媒介为主导的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媒介及其提供的信息成为人们获知外部世界、协调关系的最重要来源和依靠,媒介伦理就是“关于职业传播者在他们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的指导方针或者道德准则”。[16]职业传播者必须保证向人们输出真实的信息、客观的态度、中立的立场、迅疾的传输,完整、如实呈现人赖以生存的外部世界,增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
技术具身媒介出现后,新旧媒体之间持续融合成为媒介与传播实践的现实,媒介生产方式、传播内容、收受主体、传播环境等要素均发生了变化。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介伦理遭遇去专业主义伦理的挑战,由此引发的媒介伦理失衡“表现在媒介职业伦理上的新媒介暴力,媒介行业伦理上的过度资本化和媒介社会伦理上的泛娱乐化”等方面。 [17]
技术具身媒介不仅是新的人与世界的中介,还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整体关系,需要新的媒介伦理和价值观念来规约人与人、人与媒介、媒介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
媒介即中介,媒介也是人生存于其间的环境。技术具身媒介改变了“人”——同时成为信息的收受主体,人与媒介合为一体,传播的主体与客体混合,身份差别消失,人即传播,传播即存在。[18]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接收者之间的多重交叉且时时变换的关系,人的媒介实践和传播行为就是人全部的社会行为,因媒介形成的关系就是人所有形式的社会关系。新传播形态下,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都在各种媒介平台中迁移、共在。要使这种新型关系保持和谐,就需要培育一种新的媒介伦理,这种伦理是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即公民全体提出的要求与规约,即要求每个人具备具有全面素质的合格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具身媒介时代的媒介伦理,就是公民素养。由此,媒介伦理即社会伦理,媒介伦理也是对社会的规约,和社会治理体系无缝对接。
无论媒介形态如何变化,其作为人与人、人与世界关系中介的属性不会变化,因此,媒介伦理说到底依然是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只不过,技术具身时代,人与媒介的“互嵌”,使两者成为信息传播和关系建构的“孪生体”,两者的关系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伦理关系。
(作者:张华,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洁琪,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是2018年度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批准号:YB003)、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8LZUJBWZY096)、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科研培育项目(编号:18PY1006)的成果之一。
注释
[1][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99-300页。
[2]黄旦:《中国传播学评论(第八辑) 序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3][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9-60页。
[4]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40-441页。
[5][英]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页。
[6]黄旦:《辨音闻道识媒介》,《吉特勒论媒介·序》,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7][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8][加拿大]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5页。
[9][德]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传播媒介史绪论》,《文化研究》2013年第13期。
[10][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11]王怡红:《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2][英]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社会学基本概念(第二版)》,王修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页。
[13][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14]孙玮:《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
[15][美]J. D. 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16][美]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罗伯特·拉罗斯:《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7]刘明洋、吕晓峰:《媒介化社会视角下的新媒介伦理建构》,《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18]吕西安·斯费兹:《传播》,朱振明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0页。
责编/张晓燕
来源:《中国报业》杂志2019年12月(上)P23 -25
 | 推荐阅读频道
| 推荐阅读频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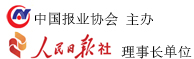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90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9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