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在电影文本的想象中,技术从“手段”变为“器官”,人的功能性被进一步延伸,人工智能、基因工程、赛博格等后人类主义范畴的存在成为显学,我们面临着一个“去肉身化”的世界;另一方面,由技术推动的影像消解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将人物化为商品,成为承载他者“欲望”的载体,人们丧失了应有的理性思考。工具理性的时代,人们应当回归于“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技术与人的关系,本文在这样的背景下,从银幕内外两个维度在伦理层面展开对技术的探讨。
【关键词】技术伦理 技术义肢 后人类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2019年,李安执导的电影《双子杀手》在万众期待中上映,这也是李安继《少年派》《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后第三次尝试高格式电影。影片上映后掀起关于技术伦理的讨论,有人认为,对技术的依赖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唯一出路;也有人认为,技术改变了人类自身的固有特性。但无可争议的是,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银幕之内的技术伦理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传统文化中用“器以载道”来体现器与道的关系,集中反映的是人与技术之间的和谐关系。“除了对技术的自然科学—技术式以及经济方面的观察外,还必须注意技术在社会心理以及社会伦理方面的影响,并有必要重现‘灵魂所具有的巨大的道德力量’”[1],技术伦理是对技术使用的后果进行伦理的反思和批判。人在对于技术的探索中,出现了作为手段的技术和作为器官的技术两个阶段,电影作为反映现实的重要工具,在对于这样两个阶段的呈现中进行了哲学化的思考,提供了探讨技术伦理的多维视角。
(一)作为手段的技术
技术是人类用来征服自然的手段。一直以来,技术外在于人的本质,人类文明的进化,离不开技术的强有力推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技术导致的结果持悲观、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现代技术将“人和世界分离”:古希腊时期,人与大地是相融的一体,技术的发展使两者对立。科技的进步建立并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展开了对“神性”的挑战。《侏罗纪公园》中,人类通过基因工程让远古灭绝生物再度复活,为已经不存在的事物“逆天改命”,违背了自然法则与历史发展的进程,导演俨然对利用科技来愉悦自我的方式进行了否定,剧情发展中也不断强调人类只有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才能实现自我生存,印证了《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技术是人类改造自身的手段。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技术是一种工具化的思维,在使用技术时,人类已经转变为以技术的方式去生存,以工具理性的方式去思考,实质是在长期使用机器的过程中,人类已经被机器和技术所统治,而当人类自己的认知不能对此进行反思时,技术便已经陷入失控,成为伦理冲突的根源所在。《头号玩家》是一部关于游戏的电影,影片用大量篇幅为观众搭建“绿洲”的秩序观,建构了一个由流行文化和亚文化组成的赛博乌托邦。2045年的世界,虚拟现实技术高度发达,玩家凭借VR眼镜等科技外设在虚拟世界中肆意穿梭,技术将游戏变成了生活,人们不仅可以在虚幻中赚取财富,赢得地位,甚至还能收获爱情,填补心灵的空缺,现实生活中的人类已经彻底被机器和技术所奴役,“绿洲”下的世界几乎将真实世界所取缔。
电影文本中,人们在不断审视和理性看待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对技术的探索应该走多远?《机械姬》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艾娃”和“京子”,前者让人类对机器产生了情感,后者则与人类发生了亲密关系,在对机器的不断优化和升级中,“人造人”向人类发起冲击,背叛了其“造物者”,人类亲手将自己推向了毁灭的深渊,剧情在剧烈反转下引发对人机伦理问题的思考。人工智能虽代表了人类科技的重大突破,但在技术只是一种外化的工具和手段的伦理考量下,人类理应采取谨慎负责的态度。如果将《失乐园》《弗兰根斯坦》和《机械姬》的文本联系在一起,那它们“都强调了科学普罗米修斯的严重问题”[2],是对作为现代性特征的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进行的有力批判,揭露了技术对伦理的颠覆和对人类存在的威胁,警示人类对知识和技术的探索应该有所界限。
(二)作为器官的技术
希腊神话中,与普罗米修斯一同用泥土创造人类的埃庇米修斯在分配生物种系属性时忘记赋予人类天生的专长,这一“遗忘”(oubli)使人类成为先天具有“原始性缺陷”[3]的存在,与其他动物相比,成为了一个没有任何可遗传的种系发生的生存技能的存在物。贝尔纳·斯蒂格勒认为技术是人内在本质的一个方面,人有技术(反自然)与自然的双重本质:正是因为埃庇米修斯的“遗忘”,人类才发明了技术这一后种系生成(épiphylogénéyique)[4]的外部器官,技术和工具成为了替代功用肢体的外部义肢(prothèse)。“人必须不断地发明、实现和创造自己的性能”[5],技术的使用决定了人类存在的根本特征和得以进化的可能,是对自身生物遗传缺失的补完。
20世纪后,出现了针对人类自身的新技术,现代化机械设备与人体的结合广泛出现在医学、军事、航空、计算机等各个领域,技术的维度包围了身体。汪民安将这样的新技术分为三种类型:人工智能(AI)、基因技术,以及有机体和无机体之间的结合——赛博格(Cyborg)。赛博格以不可思议的进化速度发展于当今工具理性至上的社会生活中,呈现出足以“摧毁人类(世界)、使人类自身非自然化(dénaturation)的力量”[6],人类的主体性在与技术结合的主客体认知过程中被逐渐磨灭,古典人文主义下纯粹肉身的边界被消解。作为后人类主义在大众文化中的想象,《阿丽塔:战斗天使》中的世界被重新编码,人类除了脑部组织尚未机械化,已成为一个类似于人体的机器,在技术的加持下变得更加强大和难以把控。《攻壳机动队》中也呈现出将人工智能、基因技术和赛博格整合为新型人类系统的可能性,实现了对生命的解构以及人类与无机物的同化,而这个系统的掌控者或系统本身,其实是民族国家,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发展实质上造就了“一个历史集权的世界”[7],赛博空间下人对自我存在和意识的主权已经丧失。不同于福柯通过制度、纪律等权力关系从外部改造身体的方式,在后人类的视域下,每个个体都是赛博格,不仅广泛存在着利用外在高科技手段拓展身体功能的普通人,还出现了渴望彻底挣脱物质性身体束缚的“超人类”(transhuman),人类面对的将是一个“去肉身化”的未来世界,无不表现出去人类中心化的症候。技术的发展一方面让人们陷入对技术的迷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技术之间复杂的伦理问题。《新世纪福音战士》中运用大量犹太教、基督教的元素,讲述了人类与使徒的战争中,人类企图用EVA(终极泛用人型决战兵器,巨机器的一种)对有“原始性缺陷”的人类进行“补完”,实现“新人类”诞生的故事,实质是对人类自身的内视与反思,是以后人类返回人类的方式,在人性的解放中重返“伊甸园”。
银幕之外的技术伦理
数字技术的成熟使数码影像得以借助计算机合成模拟(CG技术)出各种非自然可见的存在,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影像本身更加真实、更具沉浸感,甚至混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如今,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出影像中的事物是否是经过后期处理的,或者人们已经不在乎其是否真实,而是选择自觉接受。数码复制的时代,人们也不再纠结于“灵韵”(Aura)的消失与否,电影在数字技术的编织中,已经建构出一种另类的“膜拜价值”。
(一)人作为主体地位的消失
居伊·德波在上世纪60年代便预言“世界将变成影像的集合,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影像为中介”[8]。在生产力受限的年代,景观是由简单的摄影和银幕机器呈现的,人们可以轻易挣脱景观的束缚。福柯认为社会是一个规训社会而非景观社会,在当时的语境下对德波进行了批判。如今社会中的一切都在技术的推动下被图像化和景观化,景观和规训合为一体,每个人都被影像化进而景观化和商品化。
不同于传统社会历史进程中过去的时间将会成为历史,在数字化生存的当下,摄影机替代了人眼,计算机替代了人脑,人在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每一段记忆都可以像商品一样被生产出来,在播放键与暂停键的循环触控中构建永不消逝的记忆——人的意识被纳入到消费的范畴。高技术下的影像进一步干扰了人正常的线性记忆模式,过去的真实记忆将被技术制造的伪当下所不断替代,“资本所建构和控制的机器会把可以变成金钱的时间和持存通过数字化的记忆、想象和信息工业直接复制和生产出来,以建构资本所需要的‘永久性的在场’”[9]。影像的泛滥,让人们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被大大小小的屏幕所牵制,人在面对影像时的思维已经停滞,创作者带来的影像无形中“操控”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地球最后的夜晚》中,导演设置了一个长达60分钟的3D长镜头,将所有人拉入到一个被他创造的“梦境”之中,观众跟随银幕上的画面,在不自觉中戴上眼镜,从2D到3D,从现实到梦境,实现了银幕之外到银幕之内的互动,观众由此进入到被他者塑造的世界。福克斯电影公司利用Google服务器和开源AI框架创建了大数据建议系统Merlin,并用其分析了电影《金刚狼3》,对观众可能感兴趣的同类电影和元素进行预测,在20个预测样本中,有半数以上的数据认证有效。尽管Merlin的预测并不完美,但在大数据和AI框架下,创作者以“最优解”的方式激活电影票房的潜力,实现了巨额收入,电影文本不再由人的思想创作,而是转变为由技术主导的生产。他者利用技术所建构的影像凌驾于有选择能力的主体与真实需要的客体关系之上,人的真实诉求被消解,只能被动接受他者的欲望,在“诱导”中呈现出对影像的“膜拜”,丧失了原本的行动力、思考力和判断力。技术巩固了影像下的集权世界,人作为主体的地位已经丧失,“数字化的幻象成为统治”[10]。
(二)被模糊的虚拟与现实的边界
在传统技术影像中,人们可以明确自己是“看”的行为主体,是作为旁观者独立于内容之外的客体。现如今,高技术成为影像创作者追捧的对象,如李安的《双子杀手》是在全面实现数字化的基础上,综合应用4K、3D、高帧率(HFR)、高动态范围(HDR)、广色域(WCG)、沉浸式声音(Immersive Sound)等新技术实现的高格式电影,使人置身于“高清晰度”的世界,更加立体真实的画面和情景呈现成为可能。在人们对高质量视效盛宴的追求中,一切高技术在服务影像时都在创造一种逼真的“拟态环境”,观众实现了以第一人称在场者的身份沉浸在影像之中(如VR技术),VR设备的普及,使观影方式越发“私人化”——人被限制在眼镜或头盔之中,眼花缭乱的影像被直观呈现——一种内容开放却形式封闭的虚拟世界被建构出来。如此看来,《头号玩家》中的“绿洲”世界似乎愈发逼近现实,虚拟与真实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
虚拟对现实的破壁后,人的生理天性促使自身对“快感”的进一步追求。比如网络上已经出现许多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制作的情色影片、暴力游戏,人们可以在影像体验中肆意行动,且无需承担后果,过分真实的影像给色情和暴力提供了可乘之机,“第四堵墙”下的审美伦理观已被打破。斯蒂格勒认为“虚拟空间不是一个有别于现实空间的另一种空间,而是世界自我投映所借助机制的拓展,它具有前所未有的实效性,并促生了一个新的假象视域”[11]。技术呈现的影像情境替代了主体性的价值取向,人们不再依靠自身的真实经验,而是依附于影像事件的导向。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变得模糊,观众越来越相信自己看到的即是真实,沉浸式的体验弱化了道德反思的力量,人们对客观现实的正确认知也在渐行渐远。
结语
文化之所以繁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真实且不间断的交流和接触,而技术下的影像视界却在不经意间替代了真性情的传递。银幕所讲述的故事里,不论是作为手段的技术,还是作为器官的技术,都是人通过媒介反映出的精神层面的内容。伦理对主体的一系列行为进行规范,以此实现人对更高层次的追求,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触碰到现实的边界,将梦想带入到现实,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互相约束。走出银幕,技术下的幻象并非人的真实理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才是长久不变的价值意义,立足于“人”的角度,重新审视技术与人的关系,是对生命本体的再思考,实现心与物、形与神、用与美的统一,方可藏“道”于“器”,如入“有我之境”。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注释
[1]王国豫:《德国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哲学研究》,2005(05):94。
[2]郝田虎:《〈失乐园〉〈弗兰肯斯坦〉和〈机械姬〉中的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外国文学》,2019(01):8。
[3][4][5][6][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1卷,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135,244,227,106。
[7][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8][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
[9][10]张一兵,《先在的数字化蒙太奇构架与意识的政治经济学——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解读》,《学术月刊》,2017年(08):56。
[11][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3卷,方尔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83。
责编/张晓燕
来源:《中国报业》杂志2019年12月(上)P26 -28
 | 推荐阅读频道
| 推荐阅读频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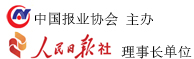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90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9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