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媒介融合 传递观 仪式观 颠覆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媒介融合”提升至国家顶层设计层面。然而,回顾近年来媒介融合的实践尝试,仍存在效果困境和商业模式困境。中宣部原部长刘奇葆在《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中提到,虽然许多传统媒体都涉足了新媒体平台,但“传统媒体业务与新媒体业务总体上还是并行的,整体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1]这种“并行”指出了媒介融合过程中过度的“技术取向”和“平台取向”,即认为开办了“两微一端”或“三微一端”就是媒介融合了,其实这构建的只是新媒体集群,各媒体平台间缺乏有效的联动,没有真正融起来,属于典型的“技术取向”型媒介融合。
习近平在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2]此次讲话强调了媒介融合在巩固共同信念、维系和连接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突出了媒介融合的“文化取向”。
未来深度媒介融合的发展方向,将突破“技术取向”型框架,转向“文化取向”型发展路径。
理论溯源:传播的“传递观”与“仪式观”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1989)曾提出两种不同的传播概念:“传播的传递观”与“传播的仪式观”。在“传递观”中,传播被“视为一种过程和技术,有时出于宗教的目的,以控制空间和人为目标,更远更快地扩散、传递和散布知识、思想和信息”,与其相联系的词汇包括“告知”(imparting)、“发送”(sending)、“传送”(transmitting)和“给别人提供信息”(giving information to others)。与“仪式观”相联系的词汇包括“分享”(sharing)、“参与”(participation)、“联系”(association)、“团体”(fellowship)和“拥有共同的信仰”(the possession of acommon faith)。“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信息在空间上的延伸,而是社会在时间上的维系;不是告知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念的表现”。可见,“传递观”下的传播强调通过技术进行传递与控制,而“仪式观”下的传播则注重通过交流实现共享、互动与连接。
虽然Carey认为这两种传播观念“不一定否认对方肯定的观点”,但不得不承认理论视角不同,则实践路径不同。媒介融合中,秉承“传播的传递观”容易导致过度的“技术取向”,即只注重媒介技术的融合和新媒体集群的构建,而“传播的仪式观”则更加关注如何促使受众更好地参与和共享融合新闻产品,如何通过媒介融合连接公众,并维系社会共同信念,从而将“融合文化”的范畴扩展至受众需求、机构组织文化和商业模式等诸多方面。
理论视野:媒介融合由“技术取向”到“文化取向”
伦敦政经学院教授罗杰·希尔维斯通(Roger Silverstone)(1995)曾提出,技术在生产和消费方面都是社会化的,如果我们想在理解媒介融合方面有所进步的话,则不能忽视“技术的社会维度”。希尔维斯通还认为,技术未来的不确定性不是来自“技术创新性”(technical inventiveness)、“容量”(capacity)、“交互性”(interactivity)、“移动性”(mobility)和“微型化”(miniaturisation)等人们所熟知的技术方面的原因,而是来自“技术作为文化的地位是不确定的”。为了修复这种不确定,希尔维斯通建议必须把包含技术创新在内的媒介融合视为一种“文化过程”。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A·迈克尔·诺尔(A. Michael Noll)(2003)强调,不能仅因为媒介数字化就认为是媒介融合了。事实上,未来取决于技术、消费者需求、商业文化、监管政策和金融等一系列元素的汇合。
美国媒介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2001)认为“媒介融合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由其引领的“数字化复兴”(digital renaissance)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秩序”,而当人们谈论媒介融合时,他们至少涉及了以下五个过程:
1.技术融合(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主要指媒介内容的数字化拓展了文字、图片和声音等媒介形式之间的潜在关系,从而使它们跨平台流动。
2.经济融合(Economic Convergence):主要指媒介机构间的横向整合,如涉足影视、书籍、音乐、游戏等产业的AOL Time Warner(在线时代华纳)。
3.社会或有机融合(Social or Organic Convergence):主要指消费者为了应付新的信息环境而使用的“多任务策略”。受众可以同时消费多种媒介形式,如看电视、写邮件、听音乐等,但这一系列活动最终都在用户的头脑中发生。
4.文化融合(Cultural Convergence):主要指媒介融合所促成的“参与型民间文化”,使新闻生产的创新形式奔涌而出。
5.全球性融合(Global Convergence):主要指由于媒介内容的全球化流通而产生的“文化杂糅”。在这种“文化杂糅”背景下,人们真正体会到自己是“地球村”的一员。
基于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君超教授(2014)指出,在“融合文化”背景下,媒体行业要从报业转型初期以技术和平台为驱动的“互联网思维”,转向媒介融合下的“融合思维”。而“融合思维”恰恰指的是“基于融合文化的特征、从新旧媒体融通性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一种大系统思维方式。它包括并超越了单纯的‘互联网思维’”。
至此,“媒介融合”的理论视野已由早期以“互联网思维”为代表的“技术取向”型框架,发展为意涵更加丰富、以“融合思维”为代表的“文化取向”型路径。
理论指导:“文化取向”型媒介融合的实践要求
“文化取向”型媒介融合超越了初期简单的“技术取向”型媒介融合,包括但不限于受众需求的重新定位、组织文化的重塑以及充分考虑机构运营成本和受众消费成本前提下商业模式的创新。
1.受众需求的重新定位
媒介融合除了鼓励受众参与新闻生产,还重塑了受众“多任务”的信息消费模式,为受众提供了“沉浸式”的信息消费体验,使受众对信息的多感官参与成为可能。媒介融合背景下,需要进行受众需求的再探究和再定位。随着媒介融合的深入推进,受众消费信息的媒介选择变得多样化,且“为争夺受众有限的注意力资源,传媒机构往往要走在用户的需求之前,各式各样的数据可视化新闻尝试就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用户对关注和理解海量现实数据的新需求”(刘沫潇,2015)。现阶段,媒介融合应以更好地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娱乐需求和思想启发需求为目标。媒介融合的要旨是更好地为受众讲述故事,在此过程中平台和技术只是辅助和手段。
2.组织文化的重塑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2012)认为三个因素决定一个组织的能力,分别是“资源”(Resources)、“程序”(Processes)和“优先顺序”(Priorities),其中“程序”与“优先顺序”构成“组织文化”。“程序”指的是“雇员将资源转换成具有更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时所采用的互动、协调、交流和决策模式”。“优先顺序”指的是“雇员判断某一活动具有吸引力与否的标准”,“程序”和“优先顺序”均有程式化风险。当组织不以“任务”(task)为驱动时,现存的组织文化很可能会对创新产生阻碍作用。
相比于人员、设备、技术等有形资源,“程序”与“优先顺序”等无形组织文化在媒体行业中固化的风险更大。媒介融合下应以具体报道任务为依据进行统筹、协调与协作,而非固有的“程序”与“优先顺序”。在《世界新闻出版商展望2017》(World News Publishers Outlook 2017)中,[3]当被问及未来一年内媒体组织需要进行的最重要的改变时,被访的近250名媒体决策者给出的排名第一的答案是对组织文化的改变。媒体机构的组织文化需要根据当下媒介融合需求进行相应的改善和提升。据报道,[4]《纽约时报》2017年宣布采用“新头版会议室”(new Page 1 room),为了培养在办公室里有关新闻报道的非正式交谈,“新头版会议室”内方形的沙发会取代现有的会议桌。透明的玻璃墙体设计和“新头版会议室”所处的地理位置将更方便编辑部内所有人的接触和使用。会议室在非使用期间将成为面向所有员工的休息室,在这里记者和编辑能够随意会面和交谈。编辑部内部空间设计是组织文化的体现,可以预想《纽约时报》的“新头版会议室”将催生更加轻松和富有创意的文化氛围,通过鼓励编辑和记者的交流沟通,更好地进行跨部门和跨平台的融合与协作。
3.商业模式的创新
“融合”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媒介融合属于广义上传媒创新的范畴。王君超、刘沫潇(2016)指出,“展望未来的‘融媒体’发展趋势,‘颠覆式创新’无疑更符合我国深度媒介融合的发展方向”。
“颠覆式创新”“颠覆性创新”或“破坏性创新”均是对克莱顿·克里斯坦森1995年提出的经济学概念“disruptive innovation”的翻译。克里斯坦森等研究者(2011)指出,“颠覆式创新”产品不是继续提升成熟产品的性能,而是“以一种更实惠、更简单的产品取代原来复杂、昂贵的产品,以便下一个更大圈子里的新客户现在有足够的金钱和技能来购买并便利地使用该产品”。
采用颠覆式创新的机构往往采取不同于主流企业的价值判断和商业模式。以“低端”新闻聚合起家的BuzzFeed用更低廉、更便捷和更通俗易懂的资讯服务开拓了新的资讯消费市场,是颠覆式创新的典型例证。曾繁旭和王宇琦(2019)认为,“颠覆性传媒创新”以“商业模式重塑为核心”,包括“产品创新”“市场定位创新”“运营流程再造”和“盈利模式创新”。未来深度媒介融合需要综合借鉴以上4种创新形式,并在充分考虑机构运营成本和受众消费成本的前提下,重塑价值网络,以更低廉的价格、常态化的生产融合新闻产品。
(作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是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依法治网背景下的“网络善治”研究》(批准号:016XCB093)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新媒介”环境下的报纸发展趋势及转型研究》(批准号:14AXW003)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刘奇葆,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检索网址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423/c1001-24930310.html,2014年4月23日。
[2]新华社,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检索网址http://www.gov.cn/xinwen/2019-01/25/content_5361197.htm,2019年1月25日。
[3]World News Publishers Outlook 2017. Retrieved from http://www.wan-ifra.org/reports/2017/09/13/world-news-publishers-outlook-2017.
[4]Dunlap,D.W.(2017,August17).What Does a Page 1 Room Look Like When Page 1 Isn’t on the Agenda.Retrieved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7/08/17/insider/what-does-a-page-1-room-look-like-when-page-1-isnt-on-the-agenda.html.
参考文献
[1]Carey,J.(1989).Communication as Culture: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Boston:Unwin Hyman.
[2]Christensen,C.M.,Horn,M.B.,Caldera,L.,&Soares,L.(2011).Disrupting College:How Disruptive Innovation Can Deliver Quality and Affordability to Postsecondary Education.Innosight Institute.Retrieved from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535182.pdf.
[3]Christensen,C.M.,Skok,D.,&Allworth,J.(2012)Breaking News Mastering the Art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Journalism.Retrieved from https://niemanreports.org/wp-content/uploads/2014/04/be_the_disrutpor.pdf.
[4]Jenkins,H.(2001).Convergence?I Diverge.Technology Review,104(5).
[5]Noll,A.M.(2003).The Myth of Convergence.JMM: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5(1).
[6]Silverstone,R.(1995).Convergence Is a Dangerous Word.Convergence,1(1).
[7]刘沫潇.媒介融合下受众需求探究[J].西部学刊,2015(13).
[8]王君超,刘沫潇.媒介融合向何处去?——基于2015年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展望[J].新闻战线,2016(1).
[9]王君超.报业转型:“互联网思维”还是“融合思维”[J].中国报业,2014(23).
[10]曾繁旭,王宇琦.重新定义传媒业的创新:持续性传媒创新VS颠覆性传媒创新[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
责编/魏艳华
来源:《中国报业》杂志2019年6月(上)P45-47
 | 推荐阅读频道
| 推荐阅读频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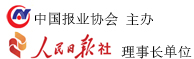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90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9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