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经过60多年演进,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构传媒业各环节,引发传媒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但人工智能是影响面广的颠覆性技术,可能带来挑战新闻传播市场准则、改变产业结构、冲击传统法规与新闻伦理、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必须重视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加强前瞻预防与伦理建构。本文着重考察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媒介发展进程中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问题,为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介伦理框架提出初步构想。
【关键词】人工智能 媒介伦理 信息茧房 深度伪造 算法推荐【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什么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之父艾伦·麦席森·图灵(AlanMathisonTuring)认为是可以自主思考的机器;人工智能的最早定义者约翰·麦卡锡(JohnMcCarthy)认为是具有人的智能化行为的机器;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主任尼尔斯·约翰·尼尔森(NilsJohnNilsson)认为是关于知识的学科;我国人工智能专家李德毅院士认为是智能科学的应用技术;传播学者李沁认为人工智能是机器、是媒介,也是未来人。中国科协审定的关于人工智能的定义认为,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技术科学。总之,关于人工智能的内涵有多种理解,在此本文基于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组织编写的《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中对人工智能界定开展研究,即人工智能是利用数字计算机或者数字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感知环境、获取知识并使用知识获得最佳结果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
人工智能对媒介产生深刻影响,乐观者认为人工智能优化了媒介环境,促进了媒介融合,推动了更多媒介新兴业态的出现,媒介的传播方式也在不断创新,传播内容更加多元,智能化成为媒介未来的发展方向。[1]悲观者则主要从媒介伦理的角度指出,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会出现信息自由传播准则被破坏、新信息沟产生、新的价值观困惑等媒介伦理问题。[2]保罗·莱文森就对人工智能对媒介的影响持警惕观点:“由人工智能所创造的新制品以及新技术与其创造者少有外部的相似性,并通常被视为阻碍、破坏而不是促进人类的发展。”[3]
在新闻实践中,“媒介伦理”与“新闻伦理”时有不加区别的混用现象,丁柏铨认为二者是相互联系又并非等价的概念,其中媒介伦理的范畴更广,不仅包括新闻伦理的内容,还包括媒介组织的相关活动。[4]总体来看,媒介伦理研究的关照主体主要是新闻从业者、媒介、受众,研究内容则聚焦在新闻真实准确、媒介公平有效、受众权利保障三个领域。4P营销理论是由杰罗姆·麦卡锡(JeromMCarthy)于1960年在美国提出,后经菲利普·科特勒(PhilipKotler)确认为市场营销组合方法,旨在通过产品、价格、推广、渠道四要素的组合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以应对市场变化。4P营销理论产生于产品至上带来产能过剩、卖方市场开始向买方市场转变的前夜,与今天人工智能时代信息过剩、新闻媒介产能过剩的发展态势极为相似。[5][6]基于此,本文着重考察的是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媒介发展进程中所带来的一系列有关媒介智能生产、智能应用、智能分发的伦理问题,因媒介营销又贯穿于生产、应用、分发三个阶段,所以本文借用4P营销理论分析人工智能时代媒介产品伦理、媒介价格伦理、媒介推广伦理、媒介渠道伦理。
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介产品伦理
传统意义上的产品一般是指通过加工、制作之后形成的物质成果,4P营销理论中的产品还包括服务等无形要素,媒介产品则是一种负载着社会“意义”的产品,它不仅使人们获得物质方面满足的体验,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人们以精神上的满足和实现。[7]媒介产品的伦理问题包含两个方面——媒介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和媒介产品本身的伦理问题。首先,媒介产品生产过程必须秉持透明性规则。在算法新闻时代,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是不透明的,即媒介生产过程更加隐秘,难以监督,生产过程透明度不高。例如,新闻生产领域的“黑箱”,即“新闻生产的幕后的幕后”[8]一直广受诟病。媒介产品的生产过程还存在伪造的过程。“深度伪造”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应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合成文本、声音、画面,从而伪造媒介产品的载体或表现形式。伪造媒介产品的过程依赖相应的算法和数据,这一过程不被公开,而隐藏在数据、算法背后的人的真实意图更是不得而知。
其次,媒介产品自身面临原创性的拷问。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发展致使新闻产品生产的规模化和自动化。[9]以机器人写作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产技术在新闻生产领域的应用,使得大量可复制的新闻作品得以集中生产,提高了新闻写作的效率。但是,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新闻产品,其原创性值得反思,特别是机器新闻写作遏制新闻作品形式的创新,不利于挖掘新闻真实性,从而扰乱新闻生产,就会出现虚假新闻、失实报道,受众永远处于“后真相时代”。例如,腾讯公司的DreamWriter机器人写作是一种程序化、固定格式性的写作,对深度报道和新闻评论无能为力。再如北京大学推出的人工智能写作机器人,基于已有的写作数据库,可以完成新闻、评论、诗词等的写作,但不可否认写作数据库的质量是其写作质量的保证。而且,智能机器人写作带来的创作便利还将模糊新闻职业的边界,人人皆可创作、人人都是记者未必是益事。基于清华大学技术支持的Giiso写作机器人免费提供给用户使用,集智能选题、智能信息收集、智能写稿、智能文章推荐等功能于一身,普通大众的参与,消解了记者的身份,模糊了新闻写作的边界。但试想,出自同一平台,依靠同一数据库的新闻稿件势必同质化严重。人工智能媒介技术也带来了版权之争,一方面涉及机器人写作的版权归属问题,另一方面是版权盗用。例如,一点资讯新闻客户端曾利用技术手段抄袭、复制他人原创内容在自己平台上播发;“西瓜视频”APP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擅自组织直播《王者荣耀》游戏并获取商业利益等侵权行为。
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介价格伦理
马克思有两种价格的定义,一是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二是价格只由购买者的购买欲和支付能力决定。[10]对此我们理解为,价格由价值决定,受供求关系影响,由于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因此生产效率要素也成为影响价格高低的重要因素。4P营销理论中的价格是指企业销售商品后所期待的回报,涉及产品定价、售价、价格促销等方面。因此,传统媒介产品价格受生产效率、供求关系、产品利润等因素的影响。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媒介产品价格除受以上因素影响外还有其特殊因素:新闻价值、特权身份、介入程度。例如华尔街日报于1996年在全球率先实行在线内容付费阅读,采取深度报道、严选题材、减少广告等措施严控新闻质量,用专业化、高品质的财经新闻内容吸引用户订阅,订阅价格从最初的每月几美元到今天的30美元左右。比利时数字出版公司Twipe的研究显示,“无阅读上限”“免费下载”“付费会员专享内容”等可以通过付费取得一定特权,成为吸引用户付费订阅媒介产品的主要动机。美联社发布的《数字时代媒体创收新途径报告》则指出,读者的参与度与付费有很大关系,参与度越高,读者越乐于接受媒体产品的价格。
由于新闻是一种媒介提供的普惠性按需享用的产品,[11]技术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服务于大众的信息获取,使新闻普惠性真正得以实现。人工智能时代媒介新闻产品不应过于小众化和专门化,新闻价值、特权身份、介入程度虽能影响媒介产品价格,但不应成为阻碍大众获取普惠性新闻产品的绊脚石。人工智能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天然优势,现实案例比比皆是,例如新闻写作机器人从新闻编写到推送,整个过程可在数秒内完成。英国科学院院士、苏塞克斯大学认知科学学院院长玛格丽特·博登(MargaretA.Boden)认为,由于人工智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此降低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应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这一优势,平抑媒介产品价格上涨趋势。部分新闻资讯类APP打着“看新闻赚现金”的旗号吸引新人下载并应用,将新闻平台吹嘘成赚钱工具,这与新闻普惠性的观念相悖。
人工智能时代媒介推广伦理
传统媒体时代,推广的主要方式有广告、公关、销售促进、人员推销,其中广告是广告主通过有偿形式在付费媒介平台传递产品或商品信息;公关则是通过相应的传播手段改善与受众之间关系而开展的一系列公共活动;销售促进是为达到短期销售目的而采取较为有效的临时性措施;人员推销是安排专职人员直接向潜在消费者进行的推销活动。在人工智能时代,媒介推广方式已出现新的变化,主要特征就是依靠大数据通过算法推荐实现精准化推广。
人工智能技术将收集到的数据与人类的自然语言进行匹配,从而进行自我学习,形成针对受众的算法推荐规则,根据受众个人喜好、媒介素养等推送新闻信息,实现了精准传播,提高了新闻信息传播效率,因此算法新闻被认为是“21世纪新闻传播领域一场全新的范式革命,不仅是对传统新闻传播方式的颠覆,更是新闻传播观念的重要突破”。[12]以澎湃新闻、今日头条、东方头条等为代表的一批新闻客户端充分利用算法优势,顺应信息个性化需求大势,针对用户特点实现信息精准传播。
算法推荐也可能促成“信息茧房”现象出现,即受众由于持续的接收与自身兴趣一致的信息从而困顿于此类信息的茧房中。例如,算法推荐在新闻报道领域会产生不透明性以及偏见,[13]更有甚者会触碰法律红线。在广告领域,依靠算法推荐技术产生的程序化广告虽能精准定位消费者进行个性化传播,但也剥夺了消费者购买产品时的选择权和知情权;同样依靠大数据技术经过算法生成的原生广告也会逾越广告与新闻的界限,广告套上新闻的外衣以至于新闻寻租,违反了基本的新闻道德。在公关、销售促进、人员推销领域,依靠大数据和算法推荐,能够实现对象的精准定位和内容的精确匹配。总体而言,依靠大数据分析,算法推荐为受众提供了“独特的信息世界”,其精准个性化的推荐功能使个体受众获取相对精确的信息,但也限制了其认知范围,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难以形成交流过程中的共同意义空间,削弱媒介的社会联系与协调功能。
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介渠道伦理
传统媒介的分发渠道建立在新闻媒体与受众之间,分发渠道单向、单一。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介借助人工智能平台实现对内容的多渠道传播,平台成为建立在新闻媒介与受众之间的桥梁,媒介、平台、受众构成网状的传播结构,受众与新闻媒介之间存在充分互动。信息传播平台、用户终端平台、媒介生产平台等成为媒介伦理失范的主要场所。例如,人工智能领域中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会收集个人行为、样貌、语音等数据信息,通过自动化机器学习进行判断分析,从而获得针对用户的数字画像,致使个人在人工智能面前成为没有隐私的“透明人”。[14]通过监控媒介信息传播过程和侵入用户终端的方式收集个人隐私信息,是最常见的情况。
在信息传播平台,“人工智能带来了把关人权利的转移”,[15]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成为事实上的信息把关人,媒介会以把关人的角色监控信息传播过程。数据是人工智能媒介赖以生存的基础,数据收集则伴随媒介信息传播全过程,因此受众在检索、阅览、反馈信息时,面临媒介的不间断监控,而人工智能媒介通过获取用户有效数据实现自我学习,从而愈发智能。脸谱Facebook曾被指控在未告知用户的前提下收集其位置信息、文本信息、商业信息等。
在用户终端平台收集隐私信息是另一种常见情况,一般通过无授权数据共享、录音、拍照等方式收集用户的密码信息、位置信息、账号信息、影像信息等。抖音APP曾将未经授权擅自获得的用户头像、昵称等信息与多闪APP进行共享,超范围传播用户个人信息,不仅损害用户权益而且损害平台利益。例如,陌陌公司“ZAO”换脸APP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在虚拟网络世界的换脸操作,同时收集用户个人隐私数据,达成一定商业目的,不仅过程隐蔽,而且严重侵犯了受众隐私权。对此,工信部曾就“ZAO”换脸APP网络数据安全问题对其进行约谈。
结语
从20世纪60年代达特茅斯会议提出人工智能至今,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两次低谷期、两次繁荣期,每一次沉浮都与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产生突破有关。再看同一时期的媒介,尤其是在两次繁荣期,媒介并未出现同步变动,只是时至今日,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深度嵌入媒介发展进程中。可以确信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只是媒介采用的技术之一,绝不是媒介生存的根本,尤其是在媒介深度融合的进程中。布莱恩·阿瑟(BrianArthur)在《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一书中所言:“技术总是进行着这样一种循环,为解决老问题去采用新技术,新技术又引发新问题,新问题的解决又诉诸于更新的技术。”因此,运用更新技术解决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介伦理问题是一种可选途径,但更新的技术也将带来新的伦理问题。
(作者:吴锋,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建森,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算法新闻”的运营机制及其传播效果监测研究(项目编号:2019N00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贾文山:《未来的传播形态:思考与前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05):76-83。
[2]胡曙光,陈昌凤:《观念与规范:人工智能时代媒介伦理困境及其引导》,《中国出版》,2019(02):11-15。
[3][美]保罗·莱文森:《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论》,邬建中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01,第1-2页。
[4]丁柏铨,陈月飞:《对新闻伦理问题的几点探究》,《新闻传播》,2008(10):4-9。
[5]杨振兵:《有偏技术进步视角下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33(08):30-46。
[6]沈浩,谈和,文蕾:《“数据新闻”发展与“数据新闻”教育》,《现代传播》,2014,36(11):139-142。
[7]姚君喜:《媒介批评:究竟批评什么——“媒介批评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8(04):1-5。
[8]仇筠茜,陈昌凤:《黑箱:人工智能技术与新闻生产格局嬗变》,《新闻界》,2018(01):28-34。
[9][日]仓桥重史:《技术社会学》,王秋菊,陈凡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12,第3页。
[10]唐思文:《对马克思价格理论的质疑》,《山东社会科学》,2007(12):60-64。
[11]赵双阁,艾岚:《经济学视角下新闻法属性定位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2):46-53。
[12]吴锋:《发达国家“算法新闻”的理论缘起、最新进展及行业影响》,《编辑之友》,2018(5):48-54。
[13]“国内外新闻与传播前沿问题跟踪研究”课题组,殷乐:《大数据时代的新闻:个案、概念、评判》,《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2(10):119-125。
[14]黄其松:《结构重塑与流程再造: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体系转型》,《贵州社会科学》,2018(01):32-37。
[15]王沛楠:《人工智能与全球新闻编辑室的转型》,《中国编辑》,2018(07):9-13。
责编/张晓燕
来源:《中国报业》杂志2019年12月(上)P16-19
 | 推荐阅读频道
| 推荐阅读频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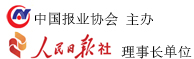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90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9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