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宾档案
刘庆鹰,1953年生于遵义红花岗区,中共党员,中央党校研究生,曾任贵州日报社遵义记者站副站长、站长、报社秘书长、副总编辑,贵州日报报业集团总经理,中国报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副主任、贵州省报业协会会长、贵州省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先后获贵州省首届十大杰出青年、贵州省劳动模范、贵州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首届新闻百佳、二级高级编辑、全国优秀总编辑、中国报业突出贡献者、省管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等荣誉;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

今年4月30日,在贵州日报报刊社表彰大会上,刘庆鹰作为老的省劳动模范应邀参会,在大会发言时对《新黔边行》进行表扬,说“年轻人比我们干得好,要把深入一线采访的精神一茬茬传下去,为时代奉献更多的好作品”。
天眼新闻文化频道:刘老师,1985年贵州日报社策划推出《黔边行》这一重磅栏目,幕后肯定有精彩故事,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刘庆鹰:1985年1月中旬,在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我作为《贵州日报》驻遵义记者站记者,在遵义访问了沿红军长征路徒步采访的《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开富同志的事迹深深感染了我,我找到报社的老领导、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陈健吾和报社社长刘学洙等,建议《贵州日报》开设类似的专栏,并恳切希望有这样的采访机会一定让我去。

刘庆鹰1985年《黔边行》采访时,拍于与赤水县城一桥之隔的四川合江县九支区。
不久,省里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套套发展贵州经济,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全省干部大会上说:我最近去了一趟赤水县。赤水离四川合江县九支区仅一桥之隔,离赤水河汇入长江的交汇处仅50多公里,大家说,像赤水这样的的县究竟是面向长江发展经济好还是面向省城贵阳发展经济好?我看按经济规律,赤水县肯定是面向长江发展经济好。我由此联想到贵州与云南、湖南、广西、四川(当时重庆未设直辖市)交界的地方,完完全全应该按经济的自然流向顺着山、顺着江、顺着河、顺着路发展经济,这样有利于加快我省对内搞活经济、对外改革开放的步伐。所以我主张黔边变前沿,把那些从省里看是“死角”的地方建成我省发展经济的“桥头堡”、对外开放的“窗口”。
对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贵州日报》编委会的同志进行了学习、讨论,也认为使黔边成为我省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加之由于交通闭塞、路途艰险,采访诸多不便,长期以来《贵州日报》对贵州边界的报道较少,更不用说深入、实地地进行系统的考察报道了。编委会遂决定在第一版推出《黔边行》专栏,并决定由我和黔东南记者站的苗族记者蒙应富同志担纲完成(每人隔天发一稿),编委会还明确《黔边行》采访我和蒙应富一个人跑半个省,我跑铜仁、遵义、毕节,蒙应富跑黔东南、黔南、黔西南,两人在六盘水各跑一半后会合。责任编辑由资深报人陈沐担任。鉴于当时交通条件所限,稿件邮寄慢,编委会指示我们的稿子通过邮局用电报发回,省邮电局专门向各地邮局发公鉴要求优先处理我们的电报稿。
天眼新闻文化频道:接到《黔边行》任务,您当时是什么心情?对《黔边行》栏目有什么认识?出发前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刘庆鹰:接到《黔边行》的采访任务,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年前几天和正月初五前,我都在紧张准备。尽管非常激动,但感觉压力很大。能不能干好?怎样去干好?我多次陷入沉思。
经反复阅读黔边各地的资料,我决定牵住边沿地区各族人民放开手脚活跃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努力增加收入这个“牛鼻子”,在抓现场目击、抓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注意四个结合:省内比与省外比相结合、新事物与新观点相结合、纵比与横比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
就这样,1985年2月26日(正月初六),我从遵义上了到铜仁玉屏的火车,27日凌晨4点,在玉屏火车站刚下车就被漫天的雨夹雪围住。车站唯一的小旅社已客满,又没有车去几里外的县城,雪愈下愈大,脚特别僵,似乎预示着此行的艰辛。但它们没有影响我的兴奋情绪,借着车站的灯光,我找了一个避雨的地方,铺开地图、翻着有关资料琢磨起来:下一步该怎么走?第一仗该怎样打?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天亮了。我开始找车进城,8点过钟,才搭上一辆去县城的马车……
天眼新闻文化频道:当年的条件有限,采访肯定是很艰辛的,您能给我们举几个小例子,回顾一下当年的景象吗?
刘庆鹰:在黔边采访的日日夜夜,开始是冬天寒气袭人,中间是雨季潮湿难挡,后来是盛夏酷暑煎熬。每日跋山涉水,经常性风餐露宿。边界上地形复杂、险要,有时两山夹峙一线天,说话听得见,走路得半天;有时峰峦叠障,一河中通,无桥无船,似乎叫你插翅难飞越。我没有怯懦,没有退缩,总是鼓足勇气,想方设法闯难关。
在毕节林口镇海嘎民族乡采访“鸡鸣三省”时(贵州毕节与云南镇雄、威信和四川叙永交界处),我意识到仅采访贵州老乡成不了稿,但遗憾的是10多天来连降暴雨,“鸡鸣三省”的渭河河水猛涨——波急浪吼、黄龙翻滚、震耳欲聋,早已不能摆渡。难道就此罢休?情急之中我想到儿时在家乡遵义湘江河涨大水时我朝上游下水,斜游到对岸的经验,于是就朝渭河上游走了300来米,然后状着胆子扑进水大得像脱缰野马般的渭河,人随波涛起伏,奋力向双手划水,终于顺着水势游到了云南的土地上,采访了云南苗族农民项炳清等人,又经过一番努力,总算完成了采访,写出了《鸡鸣——三省应人行——三省难》的稿子。参评全国新闻奖(后改为中国新闻奖)时,该稿顺利评上了三等奖。时任全国新闻奖评委、《解放军报》副总编辑杨子才说:“这是拼命三郎写的稿子!”那天,当我又斜着游回贵州这边时,惊吓、寒冷、疲倦使整个人都瘫软了,是老乡们把我扶到柴火边,休息了一个多小时才缓过气、回过神来。所以记者想出成绩,只有累得、磨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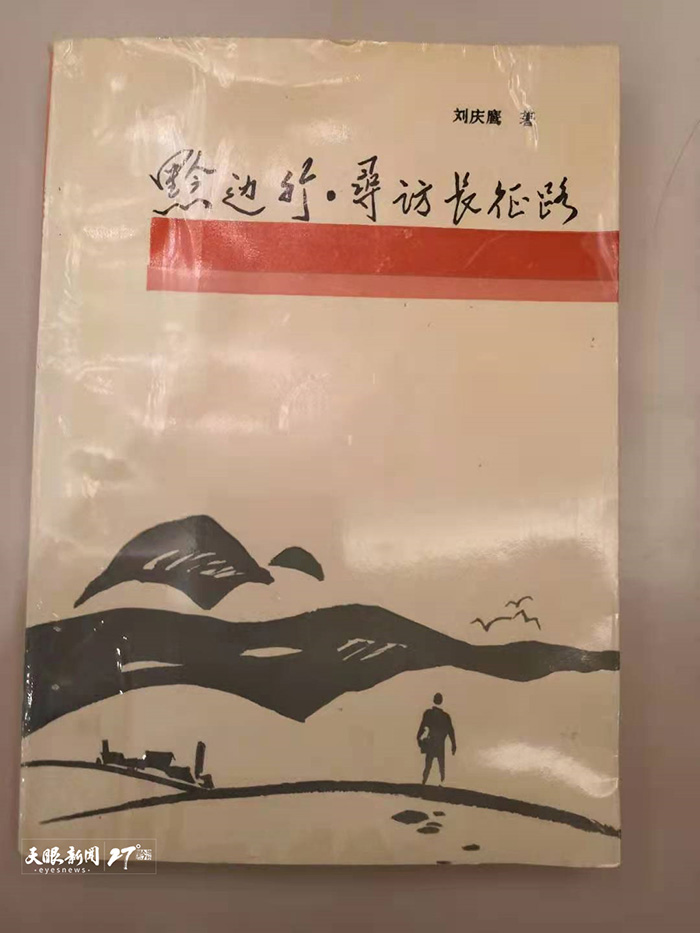
1992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刘庆鹰所著《黔边行?寻访长征路》一书。原贵州日报社社长刘学洙为该书作序。图为该书封面。
“黔边行”走路最多的一天走了100多华里,早上从六盘水发耳区岀发,走30里路到都格乡,中午从都格乡走20多里路到岔河,下午又从岔河返回都格乡,深夜再赶回发耳区(赶的原因是第二天要在发耳区参加一个重要活动),几乎走坏脚,却其乐无穷,收获了3条好稿。
那天娇阳似火。早上5点半钟,水城发耳区布依族区委书记陆清恩就把我叫醒,说天热,趁凉快赶路。发耳盛产西瓜,陆清恩从水井里捞出一个凉水镇了一晚上的西瓜,挥刀一劈两半,递一半给我,又从灶里掏出两个烤洋芋,说:“快吃,吃了好起路。”半边水镇西瓜,两个烫嘴洋芋,我第一次享受这样的早餐,边吃边咯咯地笑起来。
吃完,我和陆清恩上了路。要从发耳区走30华里的乡村公路到都格乡,奇怪的是,这条通汽车不久的路却连马车都不通了。公路上到处都是被雨水冲刷成几尺宽的深沟,一条刚修好不久的公路就这样毁掉了,原因何在?原来修路时设计人员漏掉了抗洪灾能力最强的排水沟。30里路,公路两边都没有排水沟。忽视一条沟,多遭千般罪。我以此为由头写了《没路盼路有路愁路——从水城发耳区到都格乡途中所见》的稿子,并在稿中问:全省像这样的乡村公路还有多少?接下来,我和陆清恩来到川滇交界的岔河边,看见在风雨中飘摇了15个春秋的钢丝绳吊桥非常危险,云南和贵州赶场的农民走在吊桥上,桥上经常都是二三十人,还有猪、牛、羊等牲口。桥上人多时,钢丝绳的接头处发出“嗄嘎嘎”的声音,万一钢丝绳断掉,后果不堪设想,而吊桥又是云贵两省边民赶场的唯一通道。离吊桥不到100米就是北盘江,北盘江在都格乡的土地上流了几公里,这么清澈、漂亮的河水由于不通电,无法把水引上来搞灌溉,都格乡的农民根本种不了水稻,吃不上大米,等等。于是我写了《吊桥高又险大河空自流——都格民族乡切盼培修吊桥并利用河水发电》。稿子见报后,吊桥很快得到维护。那天,我和陆清恩等在翻一座叫擦耳岩的大山时,看见农民吴正昌张贴的“寻马启事”,我便以“寻马启事”作引子,写了《“寻马启事”与黔边治安》的稿子。从早到晚虽然疲惫不堪,却苦得值得。记者的欢乐永远来自于用汗水浇灌出成功的稿件!
功夫不负,我和蒙应富合作的《黔边行》获1985年度贵州新闻奖特等奖。
天眼新闻文化频道:您当年走黔边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哪些地方?后来重访过吗?您觉得“黔边”有哪些突出的变化?
刘庆鹰:当年在黔边,我写过《三省边界一枝花川湘黔人同声夸》《农民船队远航上海》《大门朝着四川开》《早先再穷不出门而今竞渡赤水河》《岔角码头笑声满河》《“水上公共汽车”》《小砂锅大财路》《云南飞来“金凤凰”》等稿。这些新闻发生的地方,36年间我都相继重访,走进它们,就像走进一方又一方久违的亲切的家园,面对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场景(熟悉是当年的感觉,陌生是变化的精彩),我常常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它们总是在我心中激起阵阵涟漪。
譬如,1991年夏,我“寻访长征路”时,再访鸡鸣三省,见6年前呼吁的架桥尚无动静,便写了《桥影何处觅兀自空长叹——时隔6年再访鸡鸣三省》,刊登在1991年7月19日的《贵州日报》上。我在稿中写道:“鸡鸣三省的群众过去积极支援红军,为中囯革命作过贡献。而今他们赶‘穷鬼’接‘财神’却被交通不便卡住了。还要卡多久?不得而知……桥呵桥,鸡鸣三省各族人民祖祖辈辈盼望你,你何时才能架起来!”终于,去年1月21日,鸡鸣三省大桥通车了,尽管连接的是川滇,但仍给我省民众带来便利,在电视上看着横空出世的大桥,我激动不已,眼眶湿了。
譬如,《黔边行》采访时,在与四川南桐矿区山携水连的桐梓县狮溪区,我目睹在狮溪镇当过多年党委书记的梁正才因公逝世后,农民争着要用最金贵的自留地安葬他,入土时又有几千农民自发赶来给他送葬,列数他给乡亲们办的实事,许多人泣不成声,夸他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那场面太感人了,我含泪写下《数千农民给他送葬——记黔边好干部梁正才》,刊登在《贵州日报》1985年6月12日第一版。36年后的今年5月,我重返狮溪,被狮溪镇的新面貌所震撼,梁正才当年“要让老乡全部过上好日子”的愿望实现了,这是整个黔边的现状啊!面对莽莽群山,我分明看见了人民公仆梁正才的笑容。
天眼新闻文化频道:您对彭芳容的《新黔边行》有何评价?您对年轻一代的记者有何建议和期望?
刘庆鹰:今年4月30日,贵州日报报刊社党委召开“五一”劳动节先进表彰会,我作为老的省劳动模范应邀在会上发言时,对《新黔边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祝贺它取得的成功。
在我看来,《新黔边行》从选题策划到采、编、发稿,不是简单的继往开来,从形式到内容,它首先是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如果没有突破过往的勇气,没有开辟未来的方略,没有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创新意识,《新黔边行》的总体成功是不可能的。我和蒙应富搞《黔边行》时没有网络可发稿,报纸每天只有四个版面,稿子只能是千字文。而现在不同了,《新黔边行》的作者、编者与时俱进,依托发稿可以扩容的条件,运用大量的文字、图片出新出彩,使专栏稿既有声势又有实效,既有力度又有深度,立体、多元地展现了黔边的新人物、新成就、新典型、新经验、新变化,高歌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成就,涌现了一批受到广泛好评的作品。我尤为欣赏作者、编者对度的准确把握,在党性的引领下,注重了稿子的个性化、人性化、感性化和生活化,不少稿子点子新颖、选材精妙、表现独到、乡土气息浓、时代感强,读后给人启迪。真是后生可畏啊!
至于对年轻记者的建议和期望,我想与大家共勉的是:在读书学习的时候,努力将采编实践获取的材料加以提炼和概括;在采编工作中,又努力将研究书本的成果付诸实践。不断地用理论指导行动,又把行动不断地上升为理论,在这个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中,将新闻人的经验、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血肉相连。当然这其中深入一线采访是第一位的!我几十年的体会,这样做,工作中就容易产生新闻敏感,稿子的质量自然得到提高,新闻人的生命质量也由此得到升华。
辑录/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向秋樾
文字编辑/彭芳蓉
 | 传媒频道
| 传媒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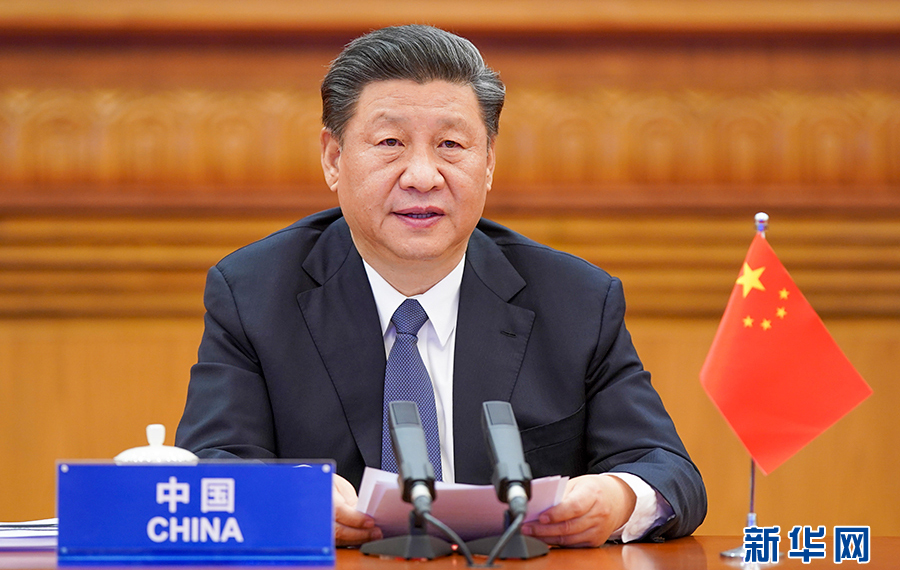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90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9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