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 建设理念 市场化 平台化 一刀切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2018年2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县域媒体要强化服务功能,整合资源,充分利用互联网,重点发展新媒体,建设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对县级媒体在舆论格局中的作用、方位做了规范。2018年8月21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2018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具体实践中,一些县级媒体没有考虑到各县的县情以及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初衷,照抄照搬长兴等地的典型经验,陷入了“一刀切”“一个样”的误区。本文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念进行辨析。

县级媒体改革必须走出“市场化”误区。很多人一说媒体改革就是“甩包袱”,把媒体推向市场,自收自支,弱化和忽略了媒体职责使命和公益性质。
课题组在为一些县进行改革咨询时深深地感受到,县级媒体改革的最简单做法就是实行企业化管理,则人员、编制、薪酬、绩效难题都能迎刃而解;但问题是,很多县级媒体缺乏足够的经济体量维持企业化管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商业规模小、层次低,缺少广告资源,不可能获得持续的经济支持。2007年甘肃玉门县各类媒体广告总收入有310万元,2015年滑落到36万元。[1]贵州省各县广播电视台陆续遭遇经济危机,经济困难导致设备老旧、人才紧缺、节目经费缺乏、节目质量差,一些节目因缺少广告而不得不停播。[2]
在一些县级媒体人看来,这一轮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大铺摊子,增员增编,财政大幅补贴,担心当地行政支持以及经济支持的可持续性。
全国县级媒体中,完全企业化的少之又少,采用的都是全额拨款或差额拨款形式。如湖南省共有89家县级广播电视台,其中全额拨款事业单位49家,差额拨款事业单位40家。[3]
作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典型,长兴传媒集团实行的是企业化管理,但这是建立在长兴县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据调研,2003年对县市报治理整顿中,因满足4个经济条件而保留下来的41家县报目前普遍情况较好。比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9家县报、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5家县报,都已成为报业颓势下集团重要的利润来源。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县报所在的县是“百强县”,媒体经济运行基础较好,而大部分县则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
实际上,即使实行企业化管理,大部分县级媒体也只能依靠政务、购买服务或者活动经营来实现,赚的也都是政府的钱。比如邳州广电的“政企云”,为政府、事业单位、国企等客户提供宣传、信息发布、数据、托管、活动、技术等服务,一年创收500多万元。长兴传媒集团的经营收入中,政务合作、活动营销、产业运营、商业广告比例为3:3:2:2,[4]其中前3项就来自政务。
在这种情况下,县级媒体实行企业化管理切忌一刀切,应因地制宜。采用公益事业单位的性质更符合县级媒体实际。当然,对于有条件的县,也可以实行企业化管理,但要采取严格意义上的事业企业“两分开”。江西分宜县融媒体中心成立后,作为全额拨款公益类事业单位,同时成立一家独立核算的经营性传媒公司,负责媒体平台的经营创收。融媒体中心与经营性公司实施彻底的两分开,用经营性公司的营收来支持融媒体中心运作。[5]
从当前县级媒体应承担的舆论与服务两种职能上看,新昌县传媒中心主任陈立新建议,财政应对公益性职能全额拨款进行事业保障,而允许服务职能进行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这是符合当前县级媒体发展实际的。
是否“平台化”
从现在已建成的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情况来看,不仅大屏幕成为标配,而且自己能够掌控的APP也成为标配。一些学者也在极力鼓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平台化”。有些县如浙江青田还拥有两个APP。一般情况下,该APP的功能是多而全的,包含了新闻、政务、民生服务板块,还会采用UGC模式,试图用APP来聚拢区域内的所有内容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但效果较差。
2016年邳州广电的“邳州银杏甲天下”APP上线,目前总装机量只有45万,但仍然摘得2017年度中国县域最强广电APP冠军。可想而知,其他县域APP的装机量、活跃用户数。同样,山东宁津的“智慧宁津”APP目前只有2万装机量,总点击量只有2200多万次,但在全国近200家与山东台轻快融媒体云平台合作的县级台点击量统计中多次排名第一。
平台化还会导致内容更加稀缺。江西贵溪市2016年10月组建了融媒体中心,目前共有11个媒体平台,2017年度传播指数位列江西省100个县的第一名,但每周只有原创稿件30余篇。[6]本来,县域范围不大,新闻素材同质化现象就比较严重,平台化需要大量内容来填充,这样的平台阅读,内容注水就越发严重。
即使是县级融媒体中心所强调的“平台”模式中,最关键的UGC账号入驻也遭遇了数量极少的问题。“邳州银杏甲天下”APP的“政企云”只吸引了不到45家乡镇企事业单位入驻。江西分宜县融媒体中心的“画屏分宜”客户端,目前也只有100多个账号入驻。但如果考虑到一个县只有二三十万人口这一现实,类似于45万的装机量、100个入驻账号已是非常努力的成果。一个县,确实没有足够支撑APP平台运行的资源。
对于APP的使用而言,施拉姆的媒介选择公式同样有效:媒体选择=媒体获得的价值/费力程度。而在平台模式下,APP用户使用人数很少时,用户加入所需要的费力程度,包括下载、时间、精力等高于其所获得的价值。只有用户达到一定规模,平台具有更高价值,才容易吸引新用户。当所获得的价值超出费力程度时,这个节点就是APP的“临界规模”。为达到“临界规模”,很多APP都动用行政手段,下载任务层层分解,从而实现“干部职工安装全覆盖”。
这样硬性安装的用户黏性很差,而且还会遭遇到“换机陷阱”。[7]县级媒体平台资源有限,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达到这个“临界规模”,这个平台就越发缺少对用户的“补偿”。因此,课题组认为,县级媒体提高服务能力,不能以APP为抓手。
从某种程度上说,县级融媒体中心最需要的是平台思维,更强调用户体验,用户的获得感,而不是纯粹的APP平台。比如,更强调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信息搜索成本、交易谈判成本和交易执行成本。不仅要关注货币成本,更要关注时间与精力等非货币形式成本。
是否“一刀切”“一个样”
中国2851个县,每个县的县情都不一样,媒体运行情况也不一样,既存在一些共性问题,也存在一些个性问题,需要区别应对,不能“一刀切”。
前车之鉴,“四级办电视”政策虽促进了县级电视台的发展,但也存在盲目建台的问题。一些县不顾本县经济情况建台,即使获批却由于条件不成熟不能开播,还有的县盲目模仿中央、省台的机构岗位设置、场地安排铺张浪费,才会导致之后的治理整顿。同样,2003年对于县级报纸一刀切的治散治滥,至今仍然为人们所诟病。很多人认为,不应以计划经济的思路来干预县报的生存与发展,是否应该拥有报纸,应由当地政府和读者需求决定。[8]这就导致治散治滥之后,大量没有公开刊号的县报纷纷创刊,在边缘中求生存。
2018年9月,中宣部在长兴召开县级融媒体中心现场会,要求全国所有县在2020年前建设好县级融媒体中心,2018年要先行建设60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有一些省份已抢在时间表前率先“完成”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任务。浙江省提出的口号是“力争2019年底实现全省全覆盖”;贵州省更快,2019年4月前,全省88个县区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全部建成;四川省也提出“183个县将于2019年建成县级融媒体中心”。
在时间表的压力下,应付现象频频出现。一些县级媒体迅速成立了融媒体中心,但往往只是简单地让新闻中心、电视台、网站等坐在一起“合署办公”,或者就直接做加法,新成立一个融媒体中心,然后让每个单位出一个人到融媒体中心坐着,甚至只是简单挂牌,搞个仪式,剪一下彩,县内各个媒体机构并没有进行整合,各媒体的机制也没有改革。[9]
实际上,每个县级媒体所处的县域经济发展情况、人口总数、城市化进度、当地媒体竞争格局,甚至包括当地行政一把手的重视度,都影响着县级媒体改革的方向与路径。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还是应该采用适合本地本单位实际情况的媒体改革举措。
(作者单位:新华出版社)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提高主流媒体新闻供给质量的扶持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17BXW09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刘勇、沙垚:《县级融媒体中心之玉门经验》,《新闻战线》2018年第17期。
[2]鲍凯、吴姣江:《关于贵州省县级广播电视发展状况的调研分析》,《中国广播》2018年第10期。
[3]张严:《县级广播电视台的出路探寻——从湖南省县级广播电视台现状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必要性》,《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年12月3日。
[4]王晓伟:《苔花初绽放小媒体要有大格局》,《三项学习教育通讯》2018年第10期。
[5]李建艳:《江西分宜:重构县级媒体建设与运行机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8年第11期。
[6]中共贵溪市委宣传部:《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巩固党的基层意识形态阵地》,《三项学习教育通讯》2018年第10期。
[7]指用户每隔一年半左右就会换手机,届时,那些使用频率低的APP不会再被安装。
[8]陈国权:《县市报整顿十年观察》,《中国记者》2013年第3期。
[9]陈国权、付莎莎:《传播力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路径》,《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1期。
责编/张晓燕
来源:《中国报业》杂志2019年6月(上)P40-42
 | 推荐阅读频道
| 推荐阅读频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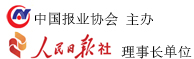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90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903号